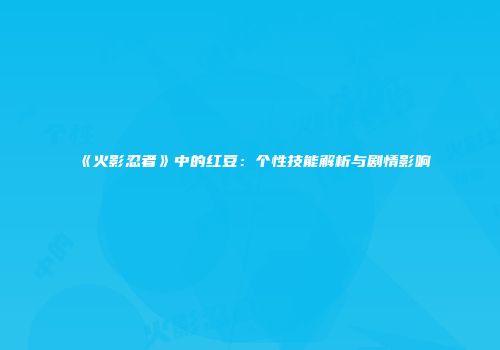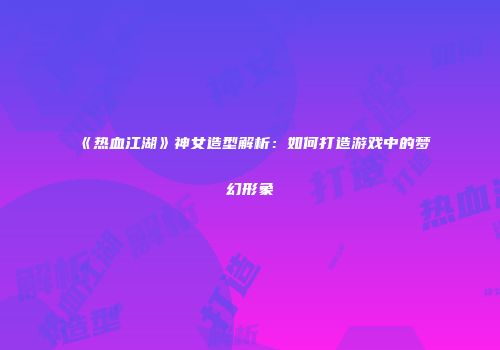猪场夜雨中的生死守护
凌晨三点的猪场亮着一盏孤灯。
李红梅蹲在产房隔间,橡胶手套上沾着血污和黏液。第三头猪崽刚落地就没了声息,母豚瘫在干草堆里,后腿不自然地抽搐着。
“胎衣滞留。”她摸到子宫内残留的胎盘碎片,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她的手说:“母猪就是咱家的活命钱,产房温度差一度,都可能要了命。”
隔壁传来丈夫王铁柱的鼾声。他总说养猪是粗活,可红梅知道,产后这七天比接生还凶险。她将葡萄糖注射液缓缓推入母豚静脉,又往食槽撒了把益母草粉。
窗外的桃花被夜雨打落,产房暖气却恒定在22℃。
第四天清晨,母豚突然拒食。红梅盯着粪便里的黄绿色黏液,抄起手机就往镇兽医站跑。“伪狂犬病抗体补了吗?”老兽医从眼镜上方瞥她,“先灌藿香正气水,再观察十二小时。”
回程的三轮车上,她抱着保温箱里的药品,想起十年前难产时婆婆煮的红糖小米粥。人和畜,到底谁更金贵?
第七天,母豚开始拱食槽。八头猪崽挤在保温箱里,皮毛泛着健康的粉光。王铁柱蹲在产房门口嘟囔:“费这老劲,直接淘汰多省事。”
红梅没接话。她看着监控屏里实时跳动的环境数据——湿度65%,氨气浓度0.15mg/m³,想起上个月猝死的养猪户老张头。
猪场东头的木棉开了,二十头新生猪崽的耳标在阳光下反光。红梅把产后护理日志锁进铁柜时,摸到抽屉深处的畜牧专业自考报名表。风从换气扇灌进来,带着青贮饲料的酸味,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春天。